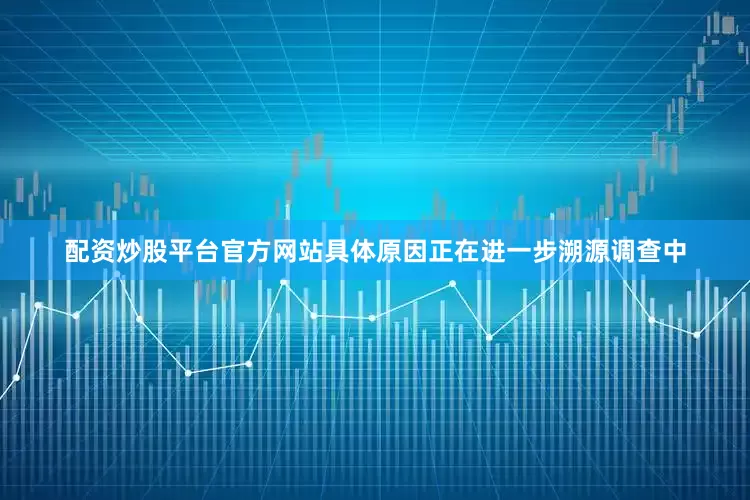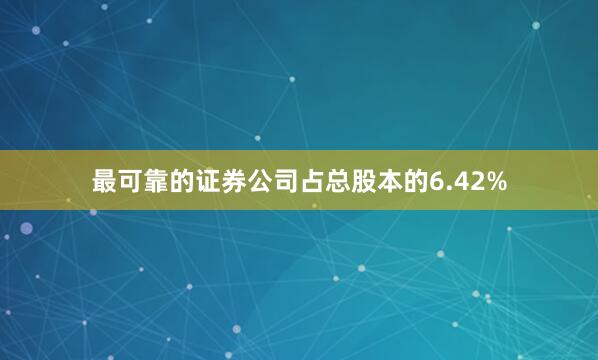日期:2025-08-24 07:28:30


朱旦华,毛远新父子的关系。
邓颖超请我上山写材料
笔者:“大跃进”时期妇女及各行各业劳动竞赛留芳历史,但“浮夸风”无疑是众矢之的。“浮夸风”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有人说是“上有所好”影响的。
朱旦华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坚决抵制虚假、夸大、空洞的作风。然而,在1958年的宣传报道中,关于粮食亩产量的虚假数据却屡见不鲜。这一现象揭示了诸多问题。以下,我将举一个具体案例,供各位研究者借鉴并由此引发更深入的思考。
1958年,正值“大跃进”运动盛夏之际,部分地区的虚报现象尤为突出。江西省妇联明确指示下派核实情况的干部务必“不见兔子不撒鹰”,未经亲眼目睹并亲自核实的数据不得上报。所有参与工作的同志均严格遵守此规定,任何违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处分。因此,妇联干部上报的数字普遍较为精确。
例如,基层干部们声称丰收在望,而妇女们试验田每亩产出的粮食数量,却让下派的干部们不得不亲自实地验收,方才肯信。基层干部们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点子”:一会儿是她们需要带孩子去看病,一会儿又声称大队会计不在,无法进行计算,企图让下派的妇女干部认可她们上报的试验田粮食产量。然而,妇联干部们却坚定地守在试验田旁,寸步不离。最终,那位基层干部不得不重新上报了试验田的实际产量。
经过对这份贴近实际的基层资料的整理,公社食堂粮食供应难以为继的状况愈发凸显,我计划将这一问题向全国妇联进行集中汇报。

恰逢其时,1959年6月28日,邓颖超同志莅临南昌,此行旨在顺道考察江西省妇联的工作,随后将赴庐山参加会议。江西省妇联的同志们对邓大姐早有耳闻,许多人更是首次得以一睹尊容,无不兴奋异常。邓大姐待人接物谦逊有礼,毫无架子,妇联的同志们毫无保留地向她汇报了所了解的情况,于是,公社食堂的问题便被提上了议程。
我搜集到一首关于公社食堂的顺口溜,特意念给邓大姐听闻:
走进食堂门,
稀稀拉拉一大盆,
锅里照见人,
碗里照见魂。
出街
裤子被扯坏。
这首民谣描绘了公社食堂供应稀饭的情景,描述得稀饭之稀,以至于回家路上竟尿意连连,既形象又生动,颇具深刻意味。邓颖超女士听闻后,不禁惊讶地问道:“果真如此?”
我沉重地点点头。
“在庐山会议期间,我们需要掌握这些详细资料。旦华,能否请你协助整理这些材料,并交给我?”
“妙极!已有许久未曾为大姐们筹备资料了。”此言勾起了我在中央妇委那段时光的美好回忆。
“请你和我一起上庐山做这份材料。”
“我不是中央委员。”我摇头。
“听闻老方已然启程攀登高峰,实属工作所迫。切记,江西省委此番担任东道主之责。”
方志纯,方志敏的胞弟,当时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并于1949年6月与朱旦华喜结连理。他早已投身山区。在这次庐山会议上,他的职责与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相仿,负责大会的安全保卫。在会议前夕,他已动员力量对庐山进行了多次细致的搜寻,甚至发现了一颗解放前未引爆的手榴弹。在邓大姐诚挚的邀请下,我于6月29日与她一同登上了庐山。

方志纯、朱旦华与毛远新
毛主席宴请曾志、水静及我。
报道:在庐山之行中,您与水静(杨尚奎前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妻子)一同下山,迎接贺子珍并与毛主席相聚?
朱旦华:几十年,很自然。
犹记我踏入山林的次日,邓大姐便前往大礼堂参与预备会议,而我则留在方志纯的居所撰写资料。我耗时五六日,将邓大姐所需之材料整理得井井有条。大约是上山后的一周光景,方志纯前来告知,毛主席将于午后邀请我共进晚餐。
惊喜地问老方:“你去吗?”
方志纯:“我不是女同志。”
我顿时欣喜若狂,竟未察觉方志纯话语中的深意。
昔日的井冈山老战友,与贺子珍情谊深厚的曾志,特地来南昌看望贺子珍。登临山巅,她向主席报告,贺子珍精神矍铄。毛主席便心生一念,欲一睹她的风采。
次日下午,于180号(美庐)处,毛主席邀请曾志、水静以及我共进晚餐。席间共四道佳肴,其中有一道青椒炒肉丝,以及一小碟炸辣椒。众所周知,江西人偏好辣味,而毛主席所品尝的菜肴更是辛辣之至。见我犹豫不决,无法动筷,主席便笑着说道:“你这上海人可得学会品尝一些辣味。”随后,他又安慰道:“江青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吃辣。”语罢,主席放声大笑,我们亦随之捧腹。
毛主席那天心情愉悦,直到饭局即将结束,他才提出:“很希望与贺子珍进行最后一次会面,该如何安排呢?”
未曾启齿,曾志的视线紧紧锁定着我。她对我和毛泽民间的联姻了如指掌。我仍旧沉默不语。水静性格直爽,语速颇快地笑言:“这事岂不轻而易举?咱们悄悄将贺大姐接到山上便是。”
主席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我心中不禁猜想,他是否在暗示我与水静一同去迎接贺子珍?在这四人之间,隐藏着一个我们共同守护的秘密。记得1949年6月,贺子珍与她的胞妹贺怡(毛泽覃的遗孀),历经辗转抵达天津,正是我和方志纯陪伴她们抵达上海。我们处理此事颇为得当,至今多年过去,各方并未因此产生较大波动和不安。尽管如此,我依旧选择缄默不言。

贺子珍、贺怡姐妹
我的思绪当时远比平静的流水要繁复得多。这或许源于我的年龄与经历,亦或是由于我身处毛泽东家族的特殊位置。我当时的想法是,毛主席若能再见贺子珍一面,那在他俩心中,无论这面相是喜是忧,都将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十年的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毛泽东先生,他是一位极重情义的人。
“当局者迷”,我想,毛主席与贺子珍二位,想必都渴望能亲见这一幕。而我,唯有默默无言。
主席直接问,“旦华同志,您怎么看?”
我只能表态:“听主席的。”
毛主席轻轻颔首,一切安排自此尘埃落定。曾志并未再对这件事进行过问。
近年来,通过阅读曾志的回忆录,我们得知此事乃陶铸所阻。曾志在文中记载:“陶铸曾言:‘若江青得知此事,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此后的发展我未曾再参与其中。最近才了解到,是朱旦华与水静同志陪同子珍一同上山拜访毛泽东。”③

陶铸、江青、曾志、毛泽东
我与贺子珍山上同宿一晚。
朱旦华:按照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周密部署,我和水静于7月7日下午两点稍过,踏上了下山之路,目的地是南昌,以便迎接贺子珍的到来。
庐山与南昌之间的距离并不算遥远,仅约200里路,当时乘车大约需时三个小时。甫一登车,水静便向我透露,杨尚奎在出发前郑重其事地强调,主席有言在先,切勿让贺子珍知晓她上山是为了与主席见面,唯恐她情绪激动,对身体造成影响。于是,我们商定以“贺子珍身为资深红军战士,江西省委特邀请她上山消暑”为由,将她接到山上。这一提议很快便得到了贺子珍的赞同。

贺子珍
7月8日午后三点,一辆小车准时抵达贺子珍在庐山的住所。无人察觉,她被悄无声息地带上了庐山,最终抵达了江西省委在牯岭涵洞左侧安排的一家隐蔽的小招待所,即“二十八号房间”。
夜幕降临,水静悄然离去,贺子珍则陷入了忙碌之中。她急于向毛主席及杨尚奎汇报并部署相关事务。我有幸陪同贺子珍,与她共居于招待所的一间卧室之中。
庐山的夜晚显得格外宁静,贺子珍轻声低语,“我真的很懊悔。”我理解地轻轻点头。
自1949年6月结识贺子珍以来,我有幸赴北京参会,期间于中央妇委的几位大姐处,探听了贺子珍离延安的缘由。毛主席与贺子珍性格皆急躁,毛主席尤以幽默风趣著称,深受延安青年们的热烈爱戴。男性青年与毛主席交谈,贺子珍持欢迎态度;然而,女青年若与毛主席久谈,便会令贺子珍心生不悦,有时甚至因此引发争执。毛主席及中央妇委的几位大姐曾多次劝导她,但贺子珍始终未能听进,心中的疑虑愈发深重。
1937年夏日之初,一位外国女记者对毛主席进行了采访。此时,中央的几位同志亦一同邀请该女记者共饮美酒。毛主席与女记者举杯互敬,恰逢贺子珍匆匆而至,她毅然伸手夺去了毛主席手中的酒杯。
主席立刻向那位女记者致以诚挚的歉意,不安地解释称我妻子缺乏相关知识,对国外的某些习俗不甚了解,恳请对方谅解。贺子珍因此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情绪激动,引发了一场风波。
夜幕降临,毛主席察觉贺子珍此举于外国记者眼中有损我党形象,遂要求她向组织进行检讨,以防止类似错误再次发生。然而,贺子珍对此难以接受,她认为毛主席是在轻视她缺乏文化素养,因而坚决拒绝检讨,愤然离开延安。她计划先赴上海就医,继而前往苏联深造,不愿让毛主席小觑她的能力。贺子珍心中还怀揣着一份愿望,那就是凭借自己的实力为党贡献更多力量,而非仅仅依赖毛主席的名号。

贺子珍和李敏
在贺子珍即将离开延安之际,毛主席深情地劝她留下,其话语间流露出的真挚情感令人动容。他言道,自己平日里不轻易落泪,却曾在三种情形下泪流满面:一是听闻穷苦百姓的悲鸣,目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心中难以自持,泪水便夺眶而出。二是与我的通信员同行,离别之际,我难舍难分,尤其是那些为国捐躯的通信员,他们的离去让我悲痛欲绝。三是当年在贵州,听闻你受伤垂危,生死未卜,那一刻,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如今,我的处境已与“左”倾路线时期迥异,我拥有了话语权。未来,我定会竭尽所能,让你不再像我过去那样,承受过多的苦难。
毛主席越是如此言辞,贺子珍便愈发觉得心中的委屈难以言表,愈发坚定了离开的决心。在情感的世界里,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陷入一种奇特的心理循环,不懂得珍惜眼前的拥有,总是渴望或追逐那些遥不可及的事物。贺子珍便是如此,她选择了离开延安。
贺子珍抵达成都不久,正值日本在上海点燃战火,使得上海的行程被迫取消。她原本计划径直前往苏联深造。毛主席再度托人传信,恳请她返回延安。蔡大姐告知,李富春当时亦在西安的八办(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中,亲自对贺子珍进行劝说,然而劝说的努力未能奏效,贺子珍坚决执意前往苏联。无奈之下,西安八办只得为她安排乘坐汽车前往兰州。毛主席再度托人送来口信,并通过电报发出邀请,希望她能返回延安,切勿前往苏联。但贺子珍对此召唤并未给予理会。贺子珍性格刚强,她坚持自己的决定,先是前往新疆迪化,随后又踏上了前往苏联的路程。

贺子珍
贺子珍于南昌疗养期间曾向我透露,毛主席三次试图留住她:首先是在抵达西安之际,通过口信和电报表达挽留之意;其次是在行至兰州时,再次发来电报坚持挽留;最后,在贺子珍抵达苏联不久后,毛泽东写信表达:“难道我们就要这样离别了吗?”贺子珍的回信简洁回应:“就此离别。”⑤
我目送贺子珍缓缓洗净面容,她仰卧于床,双眼睁得圆圆的,凝视着前方。
夜色渐浓,贺子珍默默无言,一双明亮的眸子凝视着窗外的夜色。我欲言又止,最终选择了沉默。毛泽东与毛泽民,两位皆是当世英豪,其中哥哥毛泽东的伟大尤为显著。他们兄弟之间的情感与命运,实乃可遇而不可求。若能相遇,便当倍加珍惜;若已离别,亦需学会释怀。释怀,有时亦是对事物新的领悟与珍视。忘却与珍惜,恰似庐山之巅,亦如窗外之明月清风。那种魅力,总在似曾相识却又遥不可及之间,而有意识的忘却,正是这种魅力深度的体现。
朱老,您的话诗意哲理。
朱旦华轻声说道:“傻孩子啊,真正的爱情,就如同那些充满哲理的诗篇。”
远观似岭,近望如峰,高低远近,景色各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处此山之中。此景此情,亦如人生,亦如爱情,皆然啊!
那一晚,我和贺子珍均未能入眠。直至晨曦微露,贺子珍的目光始终凝视着窗外的景色,低声而反复地吐出三个字:“我后悔。”
翌日,我并未亲自随同贺子珍前往探望毛主席。关于她如何前往、两人具体谈论了哪些内容,以及如何一同下山,这一切我均未亲自见证。

1959年7月9日之夜,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女士于美庐别墅进行了亲切会晤。
贺子珍下山大约一周之后,江青便踏上了庐山的土地。那一年,1959年,我在庐山与江青同行,一同漫步山间、定格美好瞬间,身边还伴着她的贴身护士以及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的夫人李培君。江青对此事却一无所知,她并未意识到贺子珍也已来到了庐山。

江青的护士、江青女士、朱旦华女士及李培君女士。
关于毛主席未出席庐山“全体合影”的观察与思考
朱旦华回忆道:1959年七月下旬,庐山的“神仙会”氛围逐渐变得紧张。原本江西省委为会议准备的晚间休闲舞会,很快便无人问津,而准备的电影亦鲜有人问津。与会同志们在会议期间及闲暇时刻,纷纷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争论,清晨与傍晚时分,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大声进行辩论。
全国各大省份的一把手纷纷深入基层。由于各地人民公社的发展进度不一,浮夸风与“共产风”的盛行程度各异,加之领导们的理论修养和认识深度存在差异,因此在庐山会议上出现争论在所难免,而如此激烈的争论,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中亦是较为罕见的。
自7月23日起,一种紧张的气氛逐渐笼罩四周。众人虽对究竟发生了何事一无所知,但都清楚,定然有重大事件正在悄然上演。
七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闭幕被推迟,紧接着,中央全会亦随即召开。这在党的历史长河中,堪称绝无仅有的一次盛事。
自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以来,楼前争论之声不复存在,同志们均神情凝重,目光严肃。党员的组织纪律要求严禁随意探听他人之事。直至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于午间落下帷幕,我才得知彭老总与张闻天犯了所谓的“错误”。然而,具体犯了何等“错误”,却并未有任何透露。
历经47天的盛会终于落下帷幕,负责此次会议后勤保障的江西省委同仁不禁轻舒了一口气。1959年的庐山会议,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解放思想以来中央在庐山召开的首次会议,亦是党的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中央级会议。在此次会议中,无论是参加会议的同志,还是列席旁听的嘉宾,亦或是为会议顺利举行提供各项服务的同仁,无不期盼能与中央领导一同留下合影,作为永恒的纪念。
8月16日的傍晚,我们围坐在餐桌旁享用晚餐后,便着手筹备邀请合影的事宜。杨尚奎面带微笑,吩咐我次日午后邀请毛主席与江西的同志们一同合影。他半认真半玩笑地补充道:“朱旦华去请毛主席,肯定没问题。”
我果断地摇了摇头,说道:“省委第一书记夫妇一同前往最为适宜。至于我,则应邀请周总理及邓大姐,恰巧省妇联的工作报告正需邓大姐给予宝贵意见。”
回溯往昔,我心中不禁有些忐忑,生怕在山上再次遇见主席。在与主席的数次直接交流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他是一位极为重情重义、充满人情味的领导人。主席与彭德怀将军是井冈山的老战友,历经漫长战争岁月的洗礼,他们的情谊已超越了常人的想象,变得醇厚而深远。即便在庐山上,他们对于思想认识的分歧,也并非是人们所臆测的那般翻旧账、心胸狭隘。我曾阅读过几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回忆与研究书籍,深感若脱离毛主席和彭老总那一代人共赴生死、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追求,便是对庐山会议的扭曲。当时,我认为毛主席在庐山所经历的思索与痛苦,绝不逊于彭老总。他绝不愿意在照片中留下痛苦的表情,更不会来参加与江西老表们的合影。
作者(轻轻点头):您觉得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何看法?
朱旦华表示,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历史上当之无愧的革命楷模和刚正不阿的钢铁战士;毛主席则是我国伟大的开国元勋,是引领我们党从困境走向辉煌的伟大奠基者和卓越领导者。在提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我们不应将这两位伟人视为对立双方。我们既要认识到他们在对大跃进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也要看到他们对国家和党的最高利益所展现出的无比忠诚与一致性,这样才能准确把握这次会议中冲突的实质。
1959年,我们党虽然执政了,但从战争中走出不久,横跨中国封建半封建社会的痕迹,走过战争年代的痕迹都太厚太重!党内接纳不同意见的机制不可能健全,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机制尚没能建立。不能超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来简单要求所有参加和主持庐山会议的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不能倒转历史来评价和点评历史人物,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深入洞察,庐山会议的后续影响使得毛主席对党内机制的认识愈发深刻。1965年9月,在安排彭德怀同志前往“三线”地区担任副指挥职务之际,毛主席与他见过一面,并特别强调:“真理有时隐藏在少数人的手中。”此后,毛主席又多次提倡“反潮流精神”,我认为这些都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着密切的关联。
溯至1959年8月18日的午后,江西省委成功邀请了中央政治局的多位领导。正如我所预料的,毛主席并未出席,他已于8月18日上午先行离开了庐山。我与邵省长等一同前往180别墅为其送行。在众人的坚持下,毛主席与送行人员及随行工作人员共同拍摄了一张合影,毛主席的表情略显忧郁。
午后合影时,彭总并未邀请。周总理、朱德、刘少奇等领导悉数出席,均不愿就座于预先指定的中央位置,坚持让江西省委的代表们占据前排正中。刘少奇抽着烟说道:“江西的同志们辛苦了,请各位就坐中央。”杨尚奎却表示反对。周总理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会议的工作人员是在江西省委的指导下工作的,江西省委的同志们不坐中间,似乎不太合适吧?”总理的话语引得众人欢笑。
杨尚奎竟遭遇了出人意料的局面,无奈之下,他只得请求江西的领导同志们先行就座。而我自己,竟被安置在了前排一个显眼的席位上。
“咔嚓——二——三,好了。”庐山之巅,这张珍贵的合影映照出每个人的笑容。刘少奇、周总理、杨尚奎、邵式平等人的面容,定格在这一刻。照相馆特意在照片上印上一行字:公元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庐山之巅。
晚年朱旦华
注释
①于2000年9月10日至11日,以及13日上午,笔者对朱旦华进行了多次访谈,每一次会面的地点均设在朱旦华的家中。
②于2000年9月10日之晨进行了一次访谈,并于2002年及2004年8月26日两次对此事进行了后续的交流,访谈的地点均设于朱旦华女士的住所。(访谈内容已与水静等相关人员进行了确认。)
③《革命幸存者的回忆录——曾志口述史》,第33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④据朱旦华在2000年夏季的回忆所述,毛泽东曾邀请她和曾志共进晚餐,但后来曾志却婉拒了邀请。水静独自下山迎接贺子珍。朱旦华在山上等待贺子珍的到来,并在那一晚同住一室。到了2004年,她再次提及此事,并表示自己的记忆与水静的叙述大致相符。作者在2000年、2001年和2003年期间,曾对水静进行了多次采访。
朱旦华在谈论同一事件时,表达存在细微差异。在另一次表述中,毛泽东寄往苏联的信函大意是询问两国关系是否已完全破裂。贺子珍的回应则是肯定地表示:是的。
⑥针对此问题,我曾于2000年9月、2003年5月以及2006年11月与朱旦华同志进行过深入的沟通,我们对于该问题的基本观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⑦本段内容摘自2006年11月,就本人所著《庐山档案——与名人在庐山》一书的访谈记录。
⑧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入住“美庐”,该地当年被标注为河东路180号,在山上则被称为“180”别墅。
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三月发行的《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
牛策略-实盘配资开户-在线炒股配资开户-股票配资集中网站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